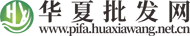您当前的位置:聚焦 > >> 正文
【世界快播报】重建作家论的写作伦理
 (资料图)
(资料图)
马征
作家论是对作家的创作道路以及重要作品进行审美的、历史的系统分析的研究成果。作家论的研究对象既可以是文学史已有定论的过往作家,也可以是当下还在写作的作家。第一次自觉的作家论写作理论倡导出现在1929年。冯雪峰在译作《社会的作家论》的《题引》中倡导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作家论的研究:“不以向来的玄妙的术语在狭小的艺术范围内工夫所谓批评的不知所以然的文章,而依据社会潮流阐明作者思想与其作品底构成,并批判这社会潮流与作品倾向之真实否,等等,这才是马克斯主义批评家的特质。” 这段话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作家论的理论基础和主要形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社会思潮分析作家的思想和作品,并给予艺术判断。随后出现了作家论写作高潮。茅盾从1927年起,先后写了《鲁迅论》《徐志摩论》《庐隐论》《落花生论》《王鲁彦论》《女作家丁玲》《冰心论》等。同时期,胡风的《林语堂论》《张天翼论》、穆木天的《徐志摩论》、许杰的《周作人论》等均是有相当影响的作家论。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则是当时马克思主义作家论的典范。除此之外,还有苏雪林的《沈从文论》、李长之的《鲁迅批判》、沈从文的《论冯文炳》《论郭沫若》《论落花生》《论施蛰存与罗黑芷》《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论穆时英》、李健吾的《关于鲁迅》、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等。这些作家论展示了不同理论资源在作家论写作上呈现出的多姿多彩。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随着新时期文学热潮的到来,再一次出现了作家论写作的高潮。1983年,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组织、编写了《当代作家论》第1卷。这是作家论写作复苏的开始,涉及了22位“在创作上卓有成就、对新时期文学作出了显著贡献,同时在艺术实践和生活实践上有着自己独特追求和探索的作家”。随后,不同类型的作家论在20世纪80年代大量出现,对当时的文学创作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近20多年来,作家论写作的数量仍然可观。但是,真正有新意的并不多见,能够引起读者共鸣的甚少,更不要说燃犀烛照、透视作家肺腑、引导时代文艺前进的了。这种状况与当下作家论写作伦理失范有一定关系。写作伦理失范表现为写作主体的态度虚假、主客体关系建立在利益交换基础上。其背后是价值标准缺失。以史为鉴,重新确立一种健康的作家论写作伦理有助于改善当下的状况,真正发挥作家论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作用。一、真诚的态度与“一般的精神法则”作家论应该遵循怎样的写作伦理?我想,首先是真诚的态度。当下作家论写作者往往缺少真诚的态度:或准备不足,率尔操觚;或王顾左右,言不由衷;更有甚者,以写作权力进行利益交换。因此,重申作家论写作的真诚态度十分必要。作家论是写作者与作家(研究对象)凭借文学作品进行心灵对话,创造出来的带有文学特性的历史研究作品。因此,作家论的写作是一个主客观相融合的实践过程。它既需要努力探求作家创作历程的历史客观性,同时又不能排斥作家论写作主体的主观性——审美体验。作为作家论写作的主观性伦理规范,作家论的写作者必须付出真诚,如同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必须以真诚的态度来感动读者一样。真诚的写作态度即写作主体在研究过程中尽己地投入个人的情感,忠实地传达自我感受和体验。作家论的写作者需要进入研究对象的精神世界,以同情之理解体验研究对象的创作动机、创作过程,再以史学家和美学家的素养忠实地传递出自己在这一过程中的感受和体验。这样,作家论的写作者才能和研究对象凭借着文学作品形成有效的对话,并借此将作家的精神世界、艺术成就以及自己的感受体验传递给读者,完成文学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循环过程。真诚的态度是沟通作家—评论家—读者的必要主观条件,三者之间任何一方缺失真诚,文学的循环链条都会被打断。沈从文在《〈现代中国作家评论选〉题记》(1934)中谈到他的作家论最自信的一点就是真诚:“我的文章没有什么惊人的地方,但每一句话必求其合理且比较接近事实。文章若毫无可取处,至少还不缺少"诚实’(不要看轻诚实,到如今的世界,看完了一本书,看懂了这个人作品,再来说话的批评家,实在就不多了!)” 沈从文对真诚的强调在其文学观中一以贯之。在《文学者的态度》(1933)中,沈从文反对作家“玩票白相”的态度,提倡一种“厚重、诚实、带点儿顽固而且也带点儿呆气的性格上”。真诚或曰“诚实”,在作家论里便是坦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不屈从、不阿附。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只有尽可能注意明确、不含糊和坦率”,才能达到文学批评“表达优秀读者的意见,促使这种意见在人群中继续传布”的目的。作家论的写作自然也是如此。作家不可能完美,坦率地指陈优劣是作家论写作者的责任。作家论的写作者应该以“优秀读者”的身份总结作家的创作历程、阐扬代表性作品的精神价值和艺术价值。一般而言,对待不在同一文学场的研究对象,写作者比较容易做到坦率直陈,但对处于同一文学场的研究对象,要做到这一点却很不容易。沈从文的《论冯文炳》(1930)是坦率直陈的典范。冯文炳的创作受周作人的影响甚深。沈从文从评价周作人的创作风格入手,指出冯文炳创作风格的渊源。沈从文肯定了冯文炳早期作品以“淡淡文字,画一切风物姿态轮廓”,表现“平凡的人性的美”的风格。这也是沈从文文学理想的一部分,但这种一致性并没有影响沈从文直率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论冯文炳》在指出他和冯文炳一致性的同时,更直接地突出二者的差异性:同样去努力为仿佛我们世界以外那一个被人疏忽遗忘的世界,加以详细的注解,使人有对于那另一世界憧憬以外的认识,冯文炳君只按照自己的兴味做了一部分所欢喜的事。使社会的每一面,每一棱,皆有一机会在作者笔下写出,是《雨后》作者(指沈从文自己——引者注)的兴味与成就。用矜慎的笔,作深入的解剖,具强烈的爱憎有悲悯的情感,表现出农村及其他去我们都市生活较远的人物姿态与言语,粗糙的灵魂,单纯的情欲,以及在一切由生产关系下形成的苦乐,《雨后》作者在表现一方面言,似较冯文炳君为宽而且优。创作基础成于生活各面的认识,冯文炳君在这一点上,似乎永远与《雨后》作者异途了。
沈从文的坦率和尽己在这里表现为直接将自己拉入论述中,甚至不免自夸之嫌。他不仅指出自己与冯文炳文学理想的差异性,而且毫不隐讳地对《莫须有先生传》趣味恶化——“把文字发展到不庄重的放肆情形下,是完全失败了的一个创作”——表示失望。同时,他把冯文炳“有意为之”的“趣味的恶化(或者这只是我个人的见解),作者方向的转变,”与他的生活环境、文学圈子联系起来,毫不客气地指出冯文炳“在北平的长时间生活”以及“周作人、俞平伯等等散文揉杂文言文在文章中”的趣味是其趣味恶化的重要因素,为这种转变所导致的“离了"朴素的美’”,“完全失去”了地方性而可惜。沈从文对冯文炳的这些评价不无可议之处,不过他的观点是他彼时真实的想法。这一方面使得《论冯文炳》敏锐地抓住并评价了冯文炳风格的特点及形成因素,另一方面使得后来的研究者可以借此探寻沈从文个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真诚是作家论写作伦理中的主观态度,但写作者的个人好恶并非作家论的客观判断标准。写作者无法彻底摆脱个人主观投入的影响,这是作家论作为文学专门史研究特点所决定的。但是,作家论有超乎个人好恶的一般标准。别林斯基说:很多人把批评理解为或是诽谤所见到的现象,或是把现象中喜好和不喜好的东西区别开来,——这是关于批评的最鄙陋的见解!在个人的喜好、信念和直觉上面,不可能肯定或否定任何东西:判断需要理性,不需要个人,个人应该代表人类的理性,而不是代表自己去判断的。……如果问题是关于历史现象、科学、艺术、道德,——那么,任何所谓我,只基于自己的感觉和意见、武断而毫无根据地判断着的我,会令人想起精神病院里的不幸的病人,他头戴着纸作的王冠,庄严而成绩卓著地治理着假想的人民,判处死刑或宽赦,宣战或媾和,好在没有人会干涉他这种天真的举动。批评——这意味着要在各别的现象里去探寻并显示该现象所据以出现的一般的精神法则,并且要确定个别现象和它的理想之间的生动的、有机的关系密切到什么程度。
别林斯基把只基于自己好恶的判断称为精神病人的呓语。他认为文学批评的评价标准是“人类的理性”,即“一般的精神法则”。在别林斯基看来,“一般的精神法则”是同时存在于作家创作和批评中的“发自时代的一种普遍精神。两者同样是时代底意识;不过批评是哲学的意识,艺术是直接的意识而已。两者有同一个内容;差别只在形式上面”。作家的创作要获得永久的价值,应该以艺术的手段蕴含“一般的精神法则”,作家论的目标就是以理性从所论作家的创作历程和作品中寻找出以艺术的直接方式存在着的“一般的精神法则”。别林斯基的“一般的精神法则”还带有先验的“绝对精神”的影子。如果把它的这一影子去掉,代之以更科学的、建立在人的社会实践基础上的历史的和审美的规律,则“一般的精神法则”就可以成为文学批评和作家论的标准。作为标准的“一般的精神法则”,在作家论写作中连接着现实与历史,其视野是超越性的,具有一般的、抽象的普遍特征;作为目标的“一般的精神法则”,在作家论写作中体现为写作主体的实践精神指向,带有写作主体和特定时空的烙印。在现代文学场域,“一般的精神法则”可以体现为多种形态的存在,但不同实践主体以“一般的精神法则”为目标的追寻精神则应该是一致的。作家论虽需要写作者有真诚的态度,但其历史品格和审美品格需要它的评判标准体现“一般的精神法则”。“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中国史家所追求的目标。史家的“一家之言”其实就是从“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中寻找出来的“一般的精神法则”。无论是作为文学史研究,还是作为文学批评,作家论也应该自觉地趋向这一目标。当然,作为文学研究,作家论的“一般的精神法则”还包含着审美规律,这是它的文学特性所规定的。沈从文在谈到批评家的“诚实”时指出:“既然是评论,应该注意到作者,作品,与他那时代一般情形。对一个人的作品不武断,不护短,不牵强傅会,不以个人爱憎为作品估价。”“评论不在阿誉作者,不能苛刻作品,只是就人与时代与作品加以综合,给它一个说明,一种解释。”沈从文所秉持的“就人与时代与作品加以综合,给它一个说明,一种解释”,就是在作家与时代的关系中探寻历史的和审美的“一般的精神法则”。自称为“明目张胆的主张感情的批评主义”的李长之,一方面极力主张以“和客观相反然而实则相成”的“感情的好恶”参与文学批评,另一方面又要批评家“把带有自己个性的情感除开,所用的乃是跳入作者世界里为作者的甘苦所浇灌的客观化了的审美能力”。李长之所以主张感情主义批评的标准是“抽去了对象,又可填入任何的对象的”“感情的型”,也是一种离弃了批评者个人好恶的一般标准。他所谓的“作者的甘苦所浇灌的客观化了的审美能力”,指向的就是作为“一般的精神法则”的审美规律。因此,李长之贯彻这一标准的《鲁迅批判》不乏真知灼见。其中对《阿Q正传》中鲁迅态度的分析就极有眼光,发人所未发。反过来这又证明了以“一般的精神法则”为标准的判断自有其深刻之处。因此,作家论写作者的真诚只有与“一般的精神法则”相结合才有价值。而这种结合的深广度与作家论写作者的主体性内涵密切相关。下文还将进一步论述。如果写作者不以“一般的精神法则”为标准,只以个人的好恶信口雌黄,则会使作家论的写作由公器变为谋私利的工具,不仅失去其历史品格,而且也脱离了文学的本性。苏雪林一生以反鲁为职志,在鲁迅逝世30年之后写的《鲁迅传论》仍无法摆脱个人意气之盛。其论在个人好恶的笼罩下全无史家所应有的“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精神。她曲解鲁迅的文章,发泄一己之厌憎情绪。她的结论形同谩骂,如称“鲁迅是一个"迫害狂’的患者”,“鲁迅的性格……阴贼、刻薄、气量偏狭、多疑善妒、复仇心坚韧强烈、领袖欲旺盛”,“鲁迅一生言行从来没有一致过”。她还认为鲁迅批判国民性是鄙视甚至仇视中华民族。此种作家论除了表现出论者之人性幽暗以外,没有任何史学价值,更不要说文学价值了。二、主客体的相善与相知主客体关系是作家论写作伦理的另一重要方面。主客体关系最有意义的情形是二者共处同一文学场。共处同一文学场意味着评论家和作家甚少时代隔膜,这是其优势所在。其弊端在于主客体双方难以摆脱现实的种种羁绊。李健吾曾指出这一写作困境:“属于同一时代,同一地域,彼此不免现实的沾著,人世的利害。我能看他们和我看古人那样一尘不染,一波不兴吗?对于今人,甚乎对于古人,我的标准阻碍我和他们的认识。”因此,共处同一文学场的作家论写作的主客体能否处理好现实利害决定着作家论写作的成败。二者良好的对话、互动有利于时代精神的认知和展开。所谓良好的对话和互动并非指作家与评论家的私交有多么亲密,而是指二者的关系应以追求“一般的精神法则”为基础。反之,如果二者关系脱离了“一般的精神法则”,建立在庸俗的利益交换基础上,则会败坏作家论的品质。建立在“一般的精神法则”基础上的作家论主客体关系,其底线是彼此抱有善意,即使彼此的观点存在差异。李长之说:“批评家和作家完全是好朋友,”批评至少应该是善意的。他的《鲁迅批判》以其感情主义的标准,对鲁迅及其主要作品做了独特的评判。当然,李长之的这一标准并非完美。他所抽象出来的“感情的型”更多是形式主义的,缺少历史的维度,以此来审视作家的创作历程容易产生凿枘不投的弊病。一旦离开了感情主义批评有限的有效性,他的评价就容易陷入非历史的判断。因此,他的判断既有前人未及的深刻,又有囿于评价标准的偏见。例如,他对鲁迅寂寞的哀感有着敏锐的剔抉,激赏鲁迅思想犀利、“情感的浓烈与真挚”、“含蓄有馀韵”的作品,又认为鲁迅“执笔於情感太盛之际”“无含蓄”“太质实”的作品是失败的。他激赏鲁迅以农村和农民为对象的作品,却对其表现都市和小市民的作品不以为然。他赞赏鲁迅的“不世故”“为人极真”,却又认为鲁迅“小资产阶级的根性很利害”,“他的为人在某一方面颇有病态”。李长之的深刻来自他对鲁迅作品的独特体味,其偏见则来自其识人尚浅以及感情主义评价标准的固有偏差。基于自信和善意,李长之在《鲁迅批判》出版前曾将其寄给鲁迅。鲁迅对此书的结论并不信服,在私下通信中,鲁迅对李长之的感情主义批评不以为然,甚至称其与“胡说乱骂”差不多。不过,鲁迅仍然“很快就写来了回信,不仅订正了书中有关著作时日,还寄赠了一张大小与明信片一般的近照”。鲁迅在给李长之的回信里,直陈《鲁迅批判》中有错误和偏见,但并不以为忤,而是加以鼓励:“即使叫我自己做起对自己的批评来,大约也不免有错误和偏见,何况经历全不相同的别人。但我以为这其实还比小心翼翼,再三改得稳当了的好。” 鲁迅与李长之的做派显然都谨守与人为善的伦理规范。鲁迅与李长之的关系并不亲密,二者的审美观也有着明显的差异。鲁迅对李长之的非历史主义观点也并不认同,却都能谨守与人为善的伦理规范,说明他们都认同批评或作家论的主客体关系应建立在“一般的精神法则”的基础上,对对方的工作给予充分的尊重。作家论创作中主客体关系比较好的例证是瞿秋白与鲁迅。瞿秋白之前,沈雁冰曾经写过《鲁迅论》。在革命文学论争中,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钱杏邨等借助新的理论武器也曾经对鲁迅进行评论,但基本上都没有真正发挥它的力量,直到瞿秋白出现。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解读鲁迅创作道路和作品的典范之作。此作因应“现时的战斗”所需,“特别指出杂感的价值和鲁迅在思想斗争史上的重要地位,”号召革命文学家们向鲁迅学习,“同着他前进”。瞿秋白从鲁迅的出身、早年经历出发,对鲁迅的创作道路做了细致的分析,剔抉出在两次“伟大的分裂”(“五四”落潮和“五卅”之后)和大革命失败之后,既与时代精神紧密联系,又带有鲜明独特性的鲁迅创作轨迹。他的结论是:“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瞿秋白提出,鲁迅的“这些革命传统(revolutionary tradition)(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韧’的战斗、反自由主义、反虚伪的精神——引者注)对于我们是非常之宝贵的,尤其是在集体主义的照耀之下”。瞿秋白的结论切中肯綮,是鲁迅论中的不刊之论。瞿秋白的独到之处还在于高度评价了当时为大多数批评者所不屑的鲁迅的杂文,称其为“战斗的"阜利通’”:“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他赞佩其中针对“军阀官僚和他们的叭儿狗”的“神圣的憎恶和讽刺的锋芒”,指出鲁迅杂文的深刻性:“不但"陈西滢’,就是"章士钊(孤桐)’等类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做社会上的某种典型。” “鲁迅杂感的特点,在那时特别显露那种经过私人问题去照耀社会思想和社会现象的笔调。”瞿秋白从思想斗争史和艺术性两个方面高度肯定了鲁迅的杂文。这一判断具有文学史家的独到眼光,奠定了鲁迅杂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瞿秋白对鲁迅的思想、创作道路作了历史的、审美的评价,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文论强大的解释力。例如,他不否认鲁迅是“士大夫阶级的子弟”,但认为鲁迅“和农民群众有比较巩固的联系”,“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这使得他真像喫了狼的奶汁似的,得到了那种"野兽性’”。“是的,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他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这一结论凸显了鲁迅思想与创作的历史价值,是前所未有的。瞿秋白的成功除了他深厚的理论素养之外,还由于他和鲁迅相知相得的亲密关系。这是其他论者无法望其项背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鲁迅书赠瞿秋白的这一条幅可以视为他们友谊最好的说明。瞿秋白写《〈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时能够随时与鲁迅进行交流。1933年2、3月间,瞿秋白在鲁迅家中避难,3月初搬至上海北四川路底日照里12号的亭子间。此住处是鲁迅代为寻找,离鲁迅住处很近。这一段时间,他们之间“有最相得的常常到深夜的漫谈。”冯雪峰认为《鲁迅杂感选集》的编选及序言的撰写均得益于此:“这工作,不能不说是他和鲁迅先生亲密接近,而且一夜一夜的漫谈的结果。秋白同志那时候就对我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和鲁迅多谈谈,又反反复复地重读了他的杂感,我可以算是了解了鲁迅了。’”稍后,杨之华、许广平也有类似的回忆。这种相知相得对作家论主客体都有益。瞿秋白写作过程中,“和鲁迅多谈谈”“反反复复地重读了他的杂感”是一种感性体验与理性思考不断互动的过程。其结果一方面,瞿秋白对鲁迅的认识得到了理论之外的生动与具体,克服了理论运用的机械性:“我可以算是了解鲁迅了”。另一方面,瞿秋白的判断也得到了鲁迅的首肯,鲁迅也借此更清晰地认识了自己:“对于《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篇论文,我觉得鲁迅先生确实发生了非常深刻的感激情绪的;据我了解,这不但因为秋白同志对于杂文给以正确的看法,对鲁迅先生的杂文的战斗作用和社会价值给以应有的历史性的估计(这样的看法和评价在中国那时还是第一次),而且也因为秋白同志也分析和批评到了他前期思想上的缺点。他谈到过这种分析和批评,说道:"分析的是对的。以前就没有人这样批评过。’说话时的态度是愉快而严肃的。”因此,《〈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可以视为作家论主客体相知相得的产物,也为作家论的写作伦理提供了一种典范:对作家的了解需要主客体不断相互认识、相互沟通交流。作家论主客体关系亲密并非现实利益相近。作家论主客体的亲密关系应该建立在基于“一般的精神法则”的共识上。鲁迅与瞿秋白的相知是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事业为基础的。冯雪峰说:“我看不出他们中间有什么可称为"私谊’的感情,”“他们的友谊的主要的根源,是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人类的共产主义的胜利而奋斗的共同的思想和行动。这是决定一切的前提条件。”在见面前,瞿秋白就写信给鲁迅,讨论翻译的信与顺以及翻译语言问题。他并非出于私人交谊,而是基于以下信念:“翻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名著,并且有系统的介绍给中国读者……这是中国普洛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他称赞鲁迅翻译苏联文学作品并非“私人的事情”,鲁迅翻译的《毁灭》“非常忠实”,“我也许和你自己一样,看着这本《毁灭》,简直非常的激动:我爱它,像爱自己的儿女一样。咱们的这种爱,一定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经历增加起来,使我们的小小的事业扩大起来。”这种出于共同理想和信念的善意使得瞿秋白和鲁迅在未见面之前就免除了庸人的礼貌,直陈己见:“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和自己商量一样。”瞿秋白和鲁迅的交谊体现出以追求真理为目标的理性。这提示我们:作家论主客体的关系建立在“一般的精神法则”的基础上,批评和创作能够获得良好的互动。建立在“一般的精神法则”基础上的主客体亲密关系不仅是作家论写作成功的条件之一,也是作家创作成功的要件之一。称职的评论家是作家的知己,甚至是作家创作的引导者。好的作家论则是作家创作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清晰地展示出作家“直接的意识”所不自觉的优点和缺点。这一点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目标之一。另外,作家的创作也在开拓着、完善着评论家的理论体系。胡风与七月派作家,尤其是与路翎的关系,是现代文学史上这样的例证之一。路翎在谈到胡风时说:“他(胡风——引者注)认为,我赞成他的理论;而他,在遇到我(而我一直在努力从事创作)之后,就找到了创作上实践的依据,我也支持了他。”路翎与胡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1939—1946)内的亲密关系对于路翎的创作和胡风的文艺理论体系的成熟都起着促进作用。因此,在理想状态下,作家论主客体能够建立基于“一般的精神法则”的共识。在此共识基础上,主客体尊重各自的工作,良性互动,使各自工作趋近时代精神。他们即使不能如瞿秋白与鲁迅、胡风与路翎那样能够深刻地体察到“一般的精神法则”,自觉地以此来规范各自的工作,至少应该遵循学术规范,不曲不阿地相处。三、重建作家论写作的伦理规范对“一般的精神法则”的探寻是作家论写作主客体形成良好伦理关系的基础。写作主体的真诚态度以及主客体关系如果缺少这一基础的支撑,作家论写作就会陷入伦理失范。因此,要救正作家论写作伦理失范的问题,应以“一般的精神法则”为核心,从写作主体和主客体关系两个方面入手解决。“一般的精神法则”是人的类本质的理性化体现。一方面,它具有人的类本质的普遍性;另一方面,类本质的普遍性与特定历史条件相结合塑造出它的时代性。别林斯基把它称为“发自时代的一种普遍精神”,就是指认了这两个特点。对于作家论写作主体而言,要从作家创作历程和重要作品中发掘带有时代性的普遍精神,需要通过较高的理论素养和自觉的主体意识才能完成。有的作家的创作历程是漫长的,经历时代的重大变迁。如最近40多年的中国文学场发生过数次巨大的变动,一些所谓“贯穿性作家”(刘心武的自称)如刘心武、王蒙、贾平凹、韩少功、王安忆、莫言等,他们的创作无一不被这些变动所塑造。面对如此波诡云谲的文学场、如此复杂的创作变化,作家论写作主体如果没有深厚的历史学和美学等素养,就无法透彻地理解这些变化,不能做到知人论世。与作家身处同一文学场的作家论写作主体的判断往往为现实的利益、策略等所遮蔽,要穿透这些现实的遮蔽,抵达“一般的精神法则 ”,需要创作主体有超越现实利益遮蔽的能力。这种能力同样来自写作主体本身。李长之的《鲁迅批判》之所以陋于识人,就是受到年龄、学识等的限制,缺少对传主所经历的时代、文学场复杂性认知的能力。由此,写作者的主体性决定着作家论的深度与广度。他的真诚及其效果与其理论素养和主体性自觉紧密相关。只有那些有能力把握“一般的精神法则”的评论家才能够从作品中发现有时候连作家也不自觉的,以直接意识存在的时代精神。缺少必要素养和能力的评论家,即使他有真诚的态度,也并不能触及作家和作品中所蕴含的“一般的精神法则”。这样的真诚也就没有什么价值。前述那些在作家论写作方面取得瞩目成就的作者,如瞿秋白、茅盾、沈从文、李健吾等,都有比较强的主体性。他们能够借由强健的主体从不同角度抓住作家文艺实践中具有时代特性的普遍精神。20世纪30年代、80年代两次作家论写作高潮均与写作者主体性高扬密切相关。当下作家论写作的伦理失范在写作主体方面表现为主体性萎顿。主体性萎顿使得写作主体缺乏透过纷繁的文学表象把握“发自时代的一种普遍精神”的能力,他们往往随波逐流,直接将现实意识作为评判的价值目标。同时,主体性萎顿还表现为以现实利益计算代替对“一般的精神法则”的追寻。庸俗的评判标准使得他们不仅不能真正地深入作家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无法做到真正的知人论世,甚至连李长之式的偏见性深刻也无法做到,自然缺少说服力和感染力。因此,救正作家论写作伦理失范的第一要点就是写作主体理论素养的提升和主体性的加强。这一问题的展开和解决是十分复杂的,本文难以完全解答。不过,有一点需要重申:“一般的精神法则”的发掘应该成为写作主体自觉追求的目标。写作者只有在这一目标追求之下才能够通过超越社会现实和自我意识的制约而感受到作为“观念的总体”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并由此而获得主体性的加强。在这一过程中,写作主体需要通过拥抱生活、与生活搏斗的主观战斗精神不断地丰富主体性的内涵,从而获得更深入地认识、理解写作客体的能力,并与客体(包括作家)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改变作家论写作的伦理失范状况还应从主客体关系角度入手,使这一关系建立在“一般的精神法则”的基础之上。当下为人所诟病的“圈子批评”“红包批评”的病因就是主客体关系失去“一般的精神法则”的支撑而被庸俗化。作家论的写作者以现实计算代替“一般的精神法则”;作为批评对象的作家也缺少相应的理论期待,缺乏心悦诚服地接受批评的胸襟。建立在利益交换基础上的庸俗关系侵蚀了作家论的品质,也使其失去了公信力。除了“圈子批评”“红包批评”,当下文学场还存在着酷评型的作家论。酷评往往只抓住作家的缺陷加以超乎批评标准的夸大,没有从历史的和审美的角度全面地评价作家及其创作。针对“圈子批评”“红包批评”,酷评也许是一剂猛药。不过,这一剂猛药并不能救正文坛乱象,相反,它本身就是文学场乱象之一。鲁迅谈到批评时曾以“剜烂苹果”来比喻好的批评家的工作:“一,指出坏的;二,奖励好的;三,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倘连较好的也没有,则指出坏的译本之后,并且指明其中的那些地方还可以于读者有益处。”酷评型作家论只做了第一步工作而放弃了其他。同时,更重要的是,酷评型作家论的写作将主客体置于对立关系,破坏了主客体之间正常的关系。这实际上就打破了文学循环的链条,对文学本身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鲁迅所期望的“剜烂苹果”的批评不是以个人好恶及占位关系来设定评价标准和主客体关系。在追求“一般的精神法则”的过程中,主客体关系被超越于现实意识的准则所塑造着,而构成一种基于真理追求的相互关系。上文所述鲁迅与瞿秋白的相知相得就是这种塑造的最好例证。更多的伦理状况是,主客体的历史观和审美观存在差异,他们的良好关系体现在各自追求“一般的精神法则”的精神一致性基础上。他们在此精神一致性基础上对各自追求的内涵和实践充分尊重,各美其美,各是其是。上述李长之与鲁迅的关系便是如此。因此,在“一般的精神法则”所规范的主客体关系中,一方面现实的利益计算策略所形成的障碍很容易被穿透;另一方面主客体的相互关系因为脱离了现实意识的羁绊,建基于更为纯粹的理性基础上而更为稳固。这种超越性的、稳固的主客体关系对于双方的工作都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撤除了许多障碍,使双方更容易走进对方的内心。这种近乎理想状态的关系是优秀的作家论产生的必要条件。要救正被败坏了的主客体关系不仅要在主客体双方确立以“一般的精神法则”为追求的伦理准则,还应该从更宏观的视野去重新建立文学场的生态秩序,以文学场独有的规范、精神准则来塑造新型的主客体关系。当下作家论写作存在的主体性萎顿、主客体关系庸俗化等伦理失范现象,与文学场的规范不健全、信仰缺失等密切相关。分工精细化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文学在社会结构中独立出来,成为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区分的领域就是这样一个现代性事件。“一般的精神法则”借助现代文学场独有的规范、精神准则、占位者关系等既塑造了作家和作家论写作者的主体性,同时也塑造着作家论的主客体关系。政治场、经济场、文化场的规范要进入文学场,必须经过文学场的规范、信仰的转译。而文学场的相对独立性一旦被破坏,这种状况下的写作主体性和主客体关系都会被侵入的其他场域规范和现实意识所塑造,失去了对文学场“一般的精神法则”的共识与追寻。这种例证在过去的文学史写作中并不鲜见。比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文学史叙事曾经以单一的阶级划分标准对作家进行定位,作家地位、重要作品评价也按照这一标准进行排列,这使得一些作家论失去了史学品格和美学价值。进入新时期之后,文学场的生态结构获得恢复,文学的相对独立性重新获得确认,由此,作家论写作者的主体性、主客体关系也获得重塑。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作家论出现又一波高潮的原因。今天,我们应该借鉴过往历史,不仅从作家论写作主体入手,期待有自觉而坚强的主体意识的写作者出现,而且应该重申文学场的特殊规范、精神准则对作家论写作伦理的深刻影响,以期恢复和重建健康的写作伦理关系。关键词:
X 关闭
X 关闭